May 18
(本文原刊於「澎湃新聞·上海書評」網站)
即便距离首次问世已有三年,“一带一路”仍可说是2016年最热门的时事议题之一。随着中国近几年在国际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国际经济上的突出表现,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交流也逐渐为海内外学界所关注。
冈田英弘:与北美“新清史”颇有渊源
冈田英弘(1931-)生于日本东京的书香世家,其父冈田正弘(1900-1993)曾在东京大学专攻医学,而后获选日本学士院会员。1950年,冈田氏进入东京大学修读东洋史学,最初跟随末松保和(1904-1992)学习朝鲜史,而后又师从日本著名蒙古学家和田清(1890-1963)学习满蒙史,从而为其后的东北亚史研究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本科毕业后,冈田英弘参与了东洋文库所主持的“满文老档”译注项目。

《内阁藏本满文老档》
日本学者所译注的“满文老档”,源于内藤湖南(1866-1934)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于沈阳盛京崇谟阁中所发现的一批以满文抄写,关于17世纪初满清入关以前的历史材料。内藤湖南发现这批材料后,将其拍摄的4300余张相片带回日本京都大学,由此奠定了日本满洲史研究的史料基础。实际上,日本学者当时所发现的“满文老档”,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手史料,而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誊写本,真正的原件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即便如此,东洋文库的“满文老档”译注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学界满洲史与清初史研究,从而培养出一代具备满文阅读能力的优秀学者。而冈田英弘本人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成长起来的。1957年,冈田英弘因参与神田信夫与松村润等人主持的“满文老档”译注工作,年仅26岁便获得日本学士院会员的殊荣,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学士院会员。
除了满洲史之外,冈田氏在蒙古学方面,造诣尤为精深。1959年至1961年间,冈田获得美国福布赖特计划(Fulbright program)的资助,前往当时的北美蒙藏学中心华盛顿大学,随蒙古学大家鲍培(Nicolas Poppe,1897-1991)进修。于1963到1965年间,又前往西德波恩大学,从蒙古学巨匠海西希(Walter Heissig,1913-2005)相论学。

蒙古学家鲍培像
从1966年到1993年这二十余年间,冈田英弘任教于东京外国语大学,直到退休。冈田这段时间指导的学生,其中较为有名的,除了他未来的人生与学术伴侣宮脇淳子(1952-)之外,还有近年美国新清史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欧立德(Mark Elliott,1968-)。学士院会员。
欧立德在伯克利大学攻读博士时,曾在1987年到1990年间,前往东外大交流,而他在日本主要的合作导师,便是冈田英弘。除此之外,冈田与欧氏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也拥有共同的学术传承,欧立德在伯克利的满文老师包森(James Bosson),也曾是鲍培的学生。正因为此,冈田氏在2013年写就的回忆录中,将欧立德视为他在美国唯一的弟子。由此看来,近二十年来北美所兴起的新清史学派,从学术谱系上来说,与冈田英弘有着相当的联系。

北美“新清史”代表人物欧立德
除了丰富的学术经历外,在著述方面,冈田英弘可以说是一位体大思精又多产的作者。其著作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如《康熙帝的信件》(1979年初版,2013年增订)、《世界史的诞生:蒙古的发展与传统》(1992年初版,1999年再版;2013年汉译)以及2010年出版的《从蒙古帝国到大清帝国》等等。此外,自2013年开始,日本藤原书店计划出版《冈田英弘著作集》8卷,目前第6卷已于2015年3月问世。这套卷帙庞大的著作集,内容涵盖中国史、内亚史、日本史乃至世界史。而这套文集,也正反映出冈田氏立足于清史,进而建构出融通东亚史,乃至于比较世界史的宏大构想。
从“满文老档”的译注工作开始,冈田英弘承袭了早年东京大学文献学派的坚实传统。很显然地,“冈田史学”并不局限于名物考订,而是以扎实的微观研究作为基础,进而试图开展普世性的宏观理论,最终回答“何谓历史”的终极关怀。总体而言,冈田英弘的历史思维主要有两项特点,即疑古的批判精神与世界史的比较视野。而冈田史学的这两项特色,与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潮,也有着相当微妙的关系。
批判精神可以说是冈田史学的精髓。不少读者在初读冈田英弘作品时,往往为其强烈的批判风格与大胆的命题假说所震慑。这样的写作风格,也正反映了冈田本人棱角分明而又颇具争议的特殊性格。也正是因为其个人特立独行的作风,相较于长期门阀化的日本学术界传统,冈田英弘的个人成就似乎很难被立刻归入到任何一个旗帜鲜明的门派当中。即便是冈田本人,亦自承在其已逾半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每有孤立之感。
何谓“蔑视派”:日本“疑古”思潮源自其汉学传统
那么在王岐山与福山的谈话中,所提及的“蔑视派”该如何放置在日本学界自身的思想语境中来理解?冈田本人的学术思想与中国学界又有何关系?
所谓的“蔑视派”,正确地来说应当是直涉日本二十世纪初以来的“疑古”思潮。而所谓的“蔑视”,指的是对充满神话色彩的日本古史,以实证方法进行批判性研究。由于强调“万世一系”的日本古史,为天皇提供了“神道设教”的正统依据,因此当学者以理性重新检视古史神话,往往被日本保守派视为一种“蔑视”民族精神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自二十世纪初以来,日本学界的“疑古”思潮与中国学界产生了深刻的互动。更精妙的是,日本“疑古”思潮的滥觞,竟是渊源自其汉学传统。
明治维新后的二十世纪初期,日本汉学界兴起了对中国古史起源进行重新检讨的风潮,正式开启了日本学界的疑古风气。有趣的是,这股深刻影响近代中日学林的思想根源,竟是源自1902年日本东洋史家那珂通世(1851-1908)对于乾嘉考据学者崔述(1740-1816)所作《考信录》的引介。而崔述的疑古辨伪之学,也从而转化成为近代日本的疑古风潮。如果说那珂通世将乾嘉学风的疑古思想引进日本,那么曾师从那珂的白鸟库吉(1865-1942),于1909年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从文献学与文字学的角度怀疑中国上古三代的真实性,可以说是为这场思想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白鸟库吉
然而白鸟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古史传说,对于日本传统的“神代”与“皇道”史观同样进行了强烈的质疑。而白鸟的弟子津田左右吉(1873-1961),则正式大张“神代史抹杀论”的旗帜,并影响了战后日本史学的主流观点。白鸟所提倡的疑古学说,不仅冲击了日本汉学与神代史传统,甚至也很有可能直接影响了1926年以顾颉刚等人为首的中国古史辨运动。
要言之,作为满鲜与中国塞外史学者,白鸟库吉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疑古学说奠定了东京大学文献学派的学术传统,并深刻地影响了二次大战以后的日本学术界。1950年代在东京大学求学的冈田英弘,正是在日本疑古思潮的背景下,继承了东京学派以文献学为基础的批判精神。而冈田英弘的批判史学,则具体体现在历史书写层面。
首先,冈田强调现代史学不应该为个人情感、神话信仰、道德价值以及意识形态所左右,史家的工作,应该是通过文本批判尽量接近历史事实。就这个标准而言,越摆脱主观价值的史学,越接近“良史”;反之,越受到特定意识形态所影响的史学,则为“恶史”。这里牵涉到一个认知上的问题,如王岐山与福山的谈话中提到,“(冈田英弘认为)中国的历史应该从司马迁说起,我认为应该从孔子说起,史记也记载了孔子。”冈田曾在著作中明确表示,他之所以将司马迁的《史记》列为中国传统史学的肇端,而不是孔子的《春秋》,原因在于后者明显的道德价值取向。换句话说,就批判史学的客观标准而言,强调道德价值判断的《春秋》不以记述史实为主要写作目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写作,因此不在其所讨论的史学传统之中。
冈田批判史学的诉求看似简单明确,实际上在进行历史书写时,却牵涉复杂的史源考订。以清朝史为例,相较于在历史事件中所自然形成的原始档案,《清实录》等官修史书中的记载很明显经过清朝官方加工,是皇朝“正统”观念下的产物。相较于当今某些学者仍将目光局限于《实录》等官修史书,冈田英弘等日本学者受到近代实证史学的影响,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关注清朝档案。冈田本人参与的“满文老档”译注,以及根据满文书信完成的《康熙帝的信件》,正是东京文献学派批判精神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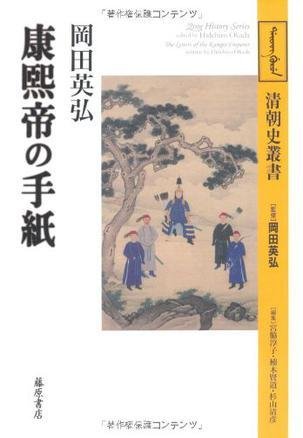
冈田英弘的著作《康熙帝的信件》
“良史”求索之难,除了史料性质的复杂考辨外,也牵涉到当代的国族认同与民族情绪。经过战后日本史学的洗礼,冈田极力反对为政治与国族情感服务的民族主义史学,从而思考超越国族界限的历史书写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冈田极力倡导消弭东洋史与西洋史的界限,强调将东亚社会置于世界史的重要性。《世界史的诞生:蒙古的发展与传统》便是冈田将其理论付诸实践的例证。在冈田的理论架构中,人类文明中,唯有西方的地中海文明与东方的中华文明发展出了历史传统。然而直到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打通东西方的藩篱,人类文明方才真正进入世界史的时代,而这也正是蒙古帝国史之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除了强调超越横向的空间维度,冈田同样也试图贯通纵向的时间维度,这也正是《从蒙古帝国到大清帝国》一书的用意。
进一步来说,冈田英弘对于世界史的推广,与追求超越民族主义的新清史学派,同样强调消解传统历史书写中的东西界限,并试图从全球史的视野重新诠释东亚文明。二者皆关注同一核心问题:如何从清史展望世界史?而这个议题背后,实际上包含了现代史学中长期争论的客观性问题:如何在全球化时代,进行超越国族界限的历史书写?这无疑是当代中国学人值得深思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