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b 6
即便距离首次问世已有三年,“一带一路”仍可说是2016年最热门的时事议题之一。随着中国近几年在国际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国际经济上的突出表现,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交流也逐渐为海内外学界所关注。
就笔者于2016年所参加的几场学术会议而言,如6月在挪威卑尔根举办之“第十四届国际藏学大会”;7月中国人民大学“汉藏佛教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张家口·冬奥会与一带一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于无锡冯其庸学术馆召开之“国学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等,不少海内外与会学者对于历史时期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密切交流,愈来愈加关注。此外,笔者于去年8月与乌云毕力格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作举办之“帝国与族群:第二届清朝与内亚工作坊”,以及在11月与滕华瑞(Gray Tuttle)教授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系主办之“一带一路:中国、内亚与东南亚的历史交流”工作坊,更是直接以探讨历史时期中国、内亚与东南亚等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为会议主旨。根据笔者参加这些会议的经验,中外学人逐步倾向将中国史放置在东亚史乃至全球史的脉络中来理解;尤其在海外学术界,以中原地区作为中国研究核心的取径,或者将中国孤立于其他周边地区的研究,已经遭遇到严重的挑战。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的口号风行于中国的当下,史学界将会如何应对并自发地产生现实关怀,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

2016年11月11-12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魏德海东亚研究所与东亚系举办之”一带一路:中国、内亚与东南亚的历史交流”工作坊。图为哥大藏学讲座滕华瑞教授开幕致辞。
就本人较为熟悉的清史与内亚研究而言,笔者以为重视内亚与海洋史的多元视角,不仅能为中国研究本身注入新的活力,更可以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对东亚、内亚与东南亚的过去与未来,提供更为深入的分析,进而反思过去中国研究中的传统范式。从这个角度来说,清史、内亚史与海洋史研究的对话与交流,不仅有助于区域研究的整合,亦能通过中国周边地区的多元视野,动态地考察“中国”这个概念的形成与历史变迁。适逢新年之际,应澎湃新闻之邀分享去年的阅读收获,笔者是以不避孤陋,从清史与内亚学的角度分享一些相关的阅读心得,并旁及海洋史研究的近期成果,尤其是对于近十年出版而尚未受到中文学界广泛关注的佳作进行简介。然而囿于识见以及行文篇幅,难免挂一漏万,尚请读者指正。
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外史学界对清帝国性质的争辩,清朝统治的内亚因素受到广泛的讨论,这也使冷战后突然消沉的内亚学重新为世人所关注。而从美国传来的 “新清史”及其所引发的学术辩论,更是蔚为风潮,甚至引起许多原本不从事清代民族史研究的中国学人,纷纷跨足清史研究,颇有指点江山之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长期耕耘档案材料,精通多语种文献的清史研究者,却反而保持相对冷静的态度,却也造成他们的研究成果,相对为中文读者所忽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吊诡的现象。尤其当“新清史”争议在中国学界炒得火热的同时,被部分中国学者视为“新清史”思想根源的日本东洋史学界,却鲜有清史研究者做出相关回应。对照“新清史”争议在中国所衍生出的激情,日本学界对于学术分歧一贯的审慎与笃实的学风,或许发人深省。在部分中国学者耗费精力怒斥“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与“历史虚无主义”的当下,日文学界在清史与满学研究上却持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日本京都大学荣誉教授河内良弘积二十余年之力,终于出版《满洲语词典》(松香堂书店,2014),为清史、满学与满文文献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读者指正。
关于中国东北民族史,京都大学教授松浦茂《清朝的黑龙江政策与少数民族》(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6)也是一部值得关注的杰作。本书作者运用《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和《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等大量满文一手史料,深刻爬梳了十七末至十九世纪清朝对黑龙江流域所进行的调查、八旗制度的引进、地方居民的集团移住以及东北毛皮贸易等课题,为探讨清廷中央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本书的第一部分,讨论尼布楚条约后清廷在黑龙江流域所进行的地理调查与国界勘定,笔者认为这些案例很可能反映出清朝作为前近代民族国家,已经具备一定的地理情报搜集整合能力以及类似于近代国境线的概念,这让笔者联想到几个相关的议题:如“国界”的概念,是否必然为西欧民族国家的产物?通观研究中俄在满洲与新疆的案例,是否有可能对作为历史产物的“国界”提供新的历史诠释?此外,关于地理认知与毛皮贸易网络的议题,似乎也可与马世嘉(Matthew W. Mosca)《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变》(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斯坦佛大学出版社,2013)与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即将出版之《皮草装点的世界:清王朝统治之下的野生生物、原始地带及自然边缘》(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斯坦佛大学出版社,2017)相互参照。

日本关于清史与内亚学的著作甚多,笔者无法一一在此细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原日本东北学院大学教授细谷良夫编《清朝史研究的新地平线:追寻田野与文书》(清朝史研究の新たなる地平―フィールドと文书を追って;山川出版社,2008)。这本论文集集结了十五篇来自日本、中国与美国清史研究者的论文,重点讨论清代八旗、清代档案中的地方社会以及清朝与蒙古等课题。本书题为“清朝史研究的新地平线”,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日本“清朝史”与“清代史”这两种取径的不同。有学者认为倾向“清朝史”研究者多半通晓满文,强调清朝在政治、文化层面的满洲特性;而“清代史”研究者则偏向使用汉文材料,侧重于明清两代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延续性。这种二分的说法或许不够精确,但也反映出重视满文文献与内亚视角的研究者,在日本清史学界可以说是雄踞一方;而侧重汉文史料的取径,仅仅是日本清史研究的一个面向。换言之,日本的清史研究并没有片面强调中原或者内亚其中一个面向,而是保持着相对多元的学术风气。有趣的是, 即便日本的“清代史”研究者多半使用汉文,却鲜有学人公开贬低满文史料的重要性,而“清朝史”研究者更是不遗余力搜集整理满文史料。反观中国学界,满文与汉文材料的使用者不仅比例悬殊,绝大多数的清史研究者对于内亚视角亦缺乏基本的认识与理解。回顾2016年,有中国学者为反对“新清史”,公开批判“满文史料的局限性”,竟把运用满文以及其他民族文字史料和“新清史”机械地画上等号,这不啻为一大憾事。中国自历史时期逐步发展为今日的多民族国家,清代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今日中国的清史研究者,若仍抱持着汉文史料独尊的心态,不能平等地看待满、蒙、藏、维等民族文献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这不仅是在学术上画地为牢,更有可能不利于建设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除了日本学者之外,近年西文学界的蒙古学与藏学研究也越来越关注内亚与清朝的交往。就笔者的阅读经验,德国波恩大学教授史卫国(Peter Schwieger)《达赖喇嘛与中国皇帝:西藏活佛转世制度的政治史研究》(The Dalai Lama and the Emperor of Chin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ibetan Institution of Reincarnation;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5)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作。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使用大量一手藏、汉文档案,通过藏、蒙、满、汉多元文化的视野,重新梳理了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过去海外藏学界中,清代西藏史是相对薄弱的环节,自伯戴克(Luciano Petech)、阿赫迈德(Zahiruddin Ahmad)等前辈学者之后,长期缺乏重大突破。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档案史料的缺乏,另一方面则是海外藏学自一九七〇年代后开始出现藏传佛教研究独大的趋势,使得不少藏学研究者对清史以及多语档案缺乏研究兴趣。然而德国波恩大学的藏学研究却曾独树一帜,在原波恩大学教授迪特·舒(Dieter Schuh)与史卫国等人的努力下,先后整理大量藏文档案,其中又以西藏功德林寺档案为大宗。根据功德林寺档案与其他已出版之藏汉文档案,史卫国成功地重构了西藏活佛转世制度以及清朝与西藏政府之间的交往过程。
另一本近年值得关注的西文藏学著作,当为四川大学副教授玉珠措姆(Yudru Tsomu)《工布朗吉在康区的兴起:瞻对的独眼龙勇士》(The Rise of Gönpo Namgyel in Kham: The Blind Warrior of Nyarong;列克星敦出版社,2015)。过去清代西藏史研究往往侧重于卫藏格鲁派上层核心,然而近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位于汉藏交界带的安多与康区的地方社会,而本书的选材也反映出藏族史研究的新动向。通过勾勒瞻对土司工布朗吉(1799-1865)的一生,作者试图通过发掘康区游牧社会的地方氏族传统,重新诠释工布朗吉与清廷的军事冲突。吉与清廷的军事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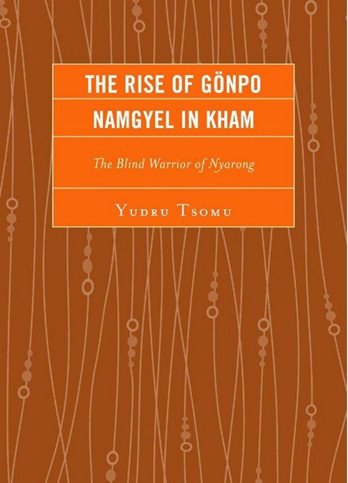
在蒙古学方面,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威斯纳·华莱士(Vesna A. Wallace)主编之《蒙古历史、文化与社会中的佛教》(Buddhism in Mongolian History, Culture, and Society;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是笔者认为较能反映近年蒙古学前沿的著作之一。这本论文集一共收录了十五篇来自历史学、人类学与宗教学等领域的蒙古学家的论文,讨论十六世纪以降佛教在蒙古各地的发展与影响。本书各篇论文的主题与方法虽相对多元,却有着共同的学术关怀,亦即强调蒙古佛教文化的主体性与异质性。过去不少学者将蒙古佛教简单地视为藏传佛教的复制品,并把蒙古佛教的发展完全归因于清朝“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政治考虑;然而本论文集通过考察佛教在蒙古的在地化及其与蒙古地方传统与族群意识的交互作用,突显了蒙古传统对佛教在地化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如本书由华莱士执笔的第五章,讨论成吉思汗形象的转变与蒙古佛教认同的发展,其中涉及蒙古地理知识与佛教世界观的相互影响,尤其是“五色四藩”与“五方佛”观念的内在理路,可以进一步参阅乌云毕力格教授与笔者所发表之《论“五色四藩”的来源及其内涵》(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近年来海外关于蒙古佛教文化的研究亦不乏佳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沙怡然(Isabelle Charleux)《朝圣中的游牧者:中国五台山中的蒙古人,1800-1940》(Nomads on Pilgrimage: Mongols on Wutaishan (China), 1800-1940;莱顿:博睿出版社,2015),以及凯洛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与呼日勒巴特尔·悟哲德(Hürelbaatar Ujeed)合著之《一个寺庙的历史:蒙古佛教的形成》(A Monastery in Time: The Making of Mongolian Buddhism;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3)。
总而言之,近年来海外蒙藏学研究一方面强调研究本体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也越来越重视内亚世界与清代中国的互动交流,而后者也可能反映在美国高校的学科划分上。近年来美国高校中为数不多的蒙藏学教席,开始在东亚系而非过去的内亚系落脚,如哥伦比亚大学的藏学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蒙古学讲座,便是突出的例子。然而这个现象是否真的代表中国崛起,将会带动美国蒙藏研究的转型,抑或仅是美国学界内部自身的学科调整,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除了与清史研究进一步结合之外,笔者认为满、蒙、藏等传统定义上的内亚学科,未来应积极地与海洋史研究展开对话,而这也是去年笔者在哥大组织一带一路工作坊的初衷。去年阅读的东亚海洋史专著中,有四本新书尤具启发,时代跨度涵盖十七至二十世纪初,也正好反映出海外学术界对清代海洋史不同时段的前沿成果。第一本为布兰迪斯大学助理教授杭行(Xing Hang)《海洋东亚中的冲突与商贸:郑氏家族与现代世界的形成》(Conflict and Commerce in Maritime East Asia: The Zheng Famil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 1620-1720;剑桥大学出版社,2015)。本书深入考察了郑氏家族在东亚海域的势力扩张及其对台湾的经营,并分析了郑氏家族在明清易代之际与西方殖民势力首次进入亚洲的历史背景下,对于东亚与东南亚海域整合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笔者对于活跃在越南与湄公河三角洲一带的明遗民势力,如杨彦迪、陈上川与鄚玖等人,及其与明郑势力的交通,尤其感到兴趣,而笔者有幸聆听杭行教授关于鄚天赐与河仙政权的精彩讲演。笔者以为,清朝与东南亚明遗民势力的交往,将是今后中越交流史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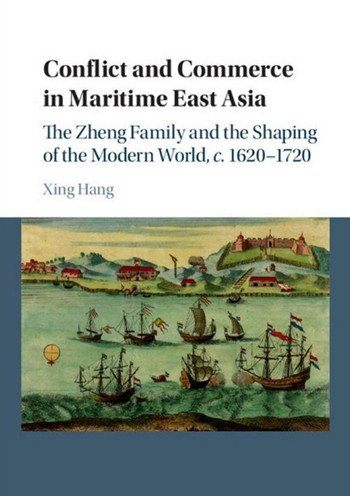
另一本关于东亚海洋史的力作,为埃默里大学教授欧阳泰(Tonio Andrade)《火药时代:世界史中的中国、军事革新与西方的崛起》(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6)。本书探讨了十三世纪以后中国与西方火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十六至十九世纪军事技术差异对中西“大分流”所产生的影响。虽然本书在方法上更接近全球史而并不局限于明清海洋史,但本书第二、第三与第四部分中关于火药技术对中西海上扩张的比较讨论,对清史研究者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除了以上两本英文新作,日文学界在海洋史方面的成果也非常值得借鉴。如信州大学准教授豊冈康史《从海贼所见之清朝:18—19世纪的南中国海》(海贼からみた清朝:十八~十九世纪の南シナ海;藤原书店,2016),通过研究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活跃于南海海域的海盗势力在闽浙粤一带的活动,以及清朝的相应措施,本书从海洋的视角对嘉庆变革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至于晚清时期华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管理、中英关系以及鸦片战争对清朝海上政策的影响,则可以参考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准教授村上卫《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福建人的活动与英国、清朝的因应》(海の近代中国―福建人の活动とイギリス・清朝;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3)。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中译本已于2016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刊行,对研究晚清海洋史的中国学者而言,是不可忽视的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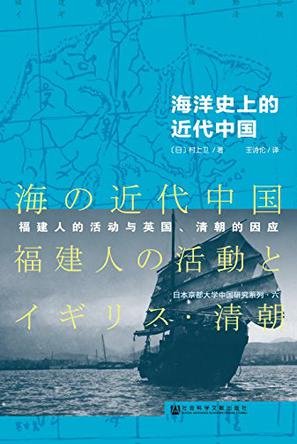
简单回顾过去一年关于清代内亚与海洋史的几本新作,以笔者管见,未来海内外的清史研究亟需与内亚学与海洋史进行整合,如此不仅能将清史研究的视野从东亚扩展至内亚与东南亚,还可能为一带一路的国家建设提供更为深入的历史分析。不仅如此,对于所谓的“新清史”争论,中国学界也不应停留在一味批判满文文献与内亚视角的层次,今人动辄耻笑清政府的“天朝”心态,清朝的遗产却从未离去。今日的学人是否能够放弃以中原为单一中心的历史叙事,不仅将左右未来中国史学界的发展,也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送走2016年,也期许我们能告别“清朝是否为中国”的争辩,因为清朝不仅属于中国,属于内亚与海洋,更属于全世界。
(本文原刊於「澎湃新聞·上海書評」網站,原题《一带一路:内亚与海洋史视角下的清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