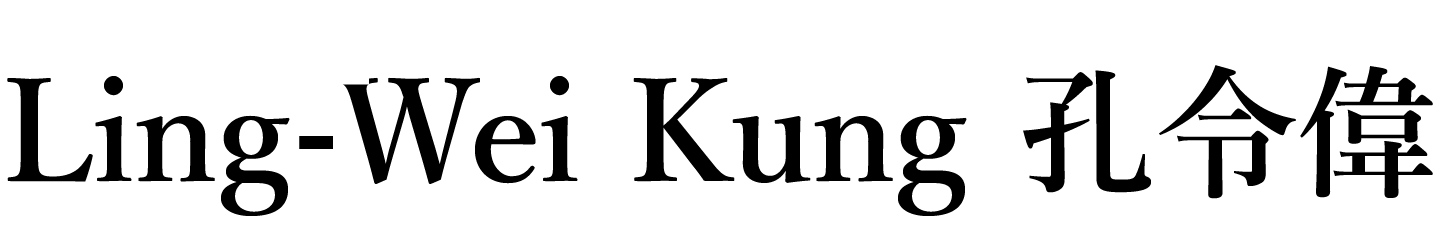《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丨蒙元史與清史的三個跨越
《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蒙古時代以降的內亞與中國》,蔡偉傑著,八旗文化2020年9月出版,332頁,新台幣450.00
近年西方製作有關中國古代話題的通俗作品中,往往將以柔然為代表的北方遊牧民,想像為與中原政權對立並覬覦所謂“絲綢之路”財富的陰險反派。有的影視及卡通作品的設定建構了“中原/內亞”、“定居/遊牧”的二元對立敘事,從角色性格、拍攝背景乃至於服裝顏色,有意無意間將中原的定居文明詮釋為忠誠、富饒與多彩。與之相對,內亞的遊牧文明在劇中則被描述為善變、貧乏與陰暗。這種將中原與內亞(Inner Asia)簡化為二元對立的敘事模式,固非西方世界的原創,卻藉由好萊塢文化資本主義的價值輸出,廣泛地在當代世界傳播。事實上這類“中原/內亞”二元對立敘事在近代的系統化根源,可以追溯至晚清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史學建構。即便近代中國數遭巨變,這類民族主義話語的幽魂卻未徹底從歷史舞台上退場;反而從鄒容、汪精衛等人的時代開始,便在中文世界中徘徊不前,迄今未能消散。“中原/內亞”的二元對立敘事,為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影響,更直接導致了東西方學術話語間的誤讀與隔閡,如近年“新清史”爭議便是其中一個顯著的例子,筆者亦曾對東西方學術話語的落差進行相關反思。
關於上述中原與內亞的史學敘事框架,近年逐漸成為中文世界眾所關注的議題,並具體反映在蒙元史與大清史這兩個學科之間的比較與延伸探討,筆者對此也曾進行過相關討論。雖然蒙元史與大清史間的延續與流變,並非一個全新話題,如日本學者岡田英弘對此早有深刻的觀察;然而隨著當代史學思潮的推進,近年中文學界的元史以及清史學者間逐漸出現一股新興的討論風潮,其中較具有代表意義的有沈衛榮的《大元史與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傳佛教研究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以及蔡偉傑的《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蒙古時代以降的內亞與中國》等新作。因前者已有相關書評多篇,為避免重複,本文以下主要評介蔡著,後將其與沉著可供相互發明之處進行比較參照。
蔡偉傑《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一書,主要收錄了作者近年關於內亞史的二十篇書評。全書主要根據評介著作的主題與時代分為三個部分,年代跨度從匈奴、蒙元到清朝。由於作者的治學興趣,篇幅主要集中在蒙元以降,而清代內亞史的部分尤其豐富。整體而言,作者的評述兼具學術性與可讀性,對國際學術前沿成果掌握相對全面,視野獨到。對於中文世界的內亞史讀者而言,本書為頗具啟發意義的評述性作品。其中部分內容雖曾在學術刊物與報章雜誌上發表,但本書內容亦進行過一定程度的增補,尤其是對多篇原見於報紙的書評增補了注釋,有利於讀者進行進一步的資料查找。
作者雖自承本書的定位為評述性的輕學術讀物,而非原創性的研究專著,然而全書的結構安排與章節行文之間,仍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作者的學術關懷。本書主標題《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一方面點出作者從世界史關照元、清中國的學術視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橫跨蒙元史與大清史的學術興趣。就世界史的歐亞格局以及元清比較視野而言,本書與沉著《大元史與新清史》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例如沉著第一章,亦從“約翰長老”等十三世紀歐洲的蒙古想像為出發討論當代蒙元史敘事,由此而言,蒙元史並不只屬於中國史的一部分,而同樣屬於歐洲史乃至於世界史的研究範疇。
就研究關懷整體而言,上述兩本著作雖有相通之處,然而就寫作體裁與學術觀點而言則不盡相同,這也反映出二者在學術背景、研究方法乃至與問題意識上的差異。相對於沉著以元明西藏為出發,蔡著則以清代蒙古為學術基礎,而二者學術立場主要的異同,也反映在其對“新清史”的評述上。如蔡著第三部分最後一章《美國“新清史”的背景、爭議與新近發展》,以及沉著第五章《我看“新清史”的熱鬧和門道》這兩篇長篇評論,應屬目前中文學界針對“新清史”爭議所作較具代表性的評述性文字。前者的亮點主要是將新清史近期發展放在美國歷史學界思潮下來理解,後者則強調從東西方學術話語之爭的角度來理解“新清史”爭議的癥結。對於想了解近年“新清史”發展與學界觀點的中文讀者而言,這兩篇評論值得比較參照。
通過比較沈、蔡二人對“新清史”評價的異同,可以總結出一個較大的歷史關懷,即從國家認同、宗教認同與族群認同三點看來,元、明、清三代政權是否具有延續性抑或是變革性?沉著根據其對元、明、清三代宮廷與藏傳佛教的觀察,主要認為藏傳佛教所代表的“內亞性”並非清朝所特有的,而基本是繼承元、明兩代的遺產。另一方面,沉著對於日本學者石濱裕美子主張清朝為“佛教政府”的觀點亦持保留態度,同時認為統治者個人的宗教認同固然重要,然而並未凌駕於清朝整體的國家認同之上。至於通觀蔡著所收錄的評論,則多見族群認同、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三者間的關係,例如其中《清代八旗制度與滿洲身份認同——評介〈滿洲之道〉》一文便是一個例子。相對於沉著,蔡著雖也強調清朝對蒙元遺產的繼承與延續,卻亦同時強調族群與身份認同的特殊性對於建構清代國家認同的關鍵作用。二者在學術觀點上的側重不同,一方面除反映其治學關懷的差異,另一方面或許也體現出語文學與歷史人類學思潮對於元、清史學者所產生的不同啟發。
通觀上述兩本著作,筆者認為將來中文學界的研究者無論對於“內亞性”“新清史”或者“多語種史料”等議題抱持著什麼立場觀點,關鍵仍在於維持學術討論的開放性與多元性,而非強調立場過硬地武斷站隊,這也是上述兩本著作所具有的示範意義。正如王國維《國學叢刊序》所言:“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學術觀點討論本無分東西新舊,如果必須片面強調特定立場的獨尊地位,反而失去了學術的開放性而容易導致思維固化,進而落入所謂信息繭房的誤區。
根據以上的觀察,筆者認為蒙元史與大清史的比較討論與學術對話的基礎,可以總結為“三個跨越”,即跨地域、跨斷代、跨文明,而這也正是筆者過去在評價中國史、內亞史、歐亞史乃至於世界史著作的一貫立場。所謂跨地域的格局,即是將元、清中原與內亞地區的交流,不僅視為中國史更是世界史的一部分。關於跨斷代的視野,則是反思過去以“中原正朔”為核心的一元化斷代史書寫,同時關注內亞多元社群文化的內在延續性。至於跨文明的關懷,則是將不同文明在歷史舞台上的多元角色等量齊觀,而非片面強調單一文明或者單一語文對於重構中國史乃至於世界史的優越性,避免陷入本文開頭所謂二元對立式的歷史敘事謬誤。如何通過實踐“三個跨越”,進而維繫蒙元史以及大清史敘事的開放性,將是中文學界與讀者們需要一同努力的目標。